《水滸傳》第一反派高俅(?-1126)事蹟新考
北宋武將中,廣為大眾所知而臭名四播的,《水滸傳》的第一反派高俅高大尉,可說是數一數二。在與《水滸傅》有開的戲曲、電影、電視劇渲染下,高俅給人的印象,是比以蔡京(1047-1126)為首的「宣和六賊」還要壞。高俅在小說中,具體幹的壞事,大陸的《水滸傅》學者王利器 (1912一1998)教授概括為「逼走王進,陷害林沖,排斥楊志,進攻宋江」1。 至於他在小說裹的下場,《水滸傅》續書《水滸後傳》寫他在靖康之難後,被劫後餘生的梁山好漢砍殺於中牟縣(今河南中车縣)。2小說家言與歷史事實自然有很大的出入,宋史上的高俅,雖確是出身宋徽宗(1100—1125 在位)藩邸,受徽宗寵信而掌禁旅多年的佞臣:但他既非横死,亦與梁山好漢無直接糾葛。關於高俅的真實事蹟,據王利器教授之研究,早在清代,王士植 (1634-1711)、阮葵生 (1727-1789)及俞樾(1821—1906)等三人,已注意到南宋人王明清 (1127一1215後)《揮麈錄•後錄》一則不足三百八十字、簡述高俅一生事蹟的筆記,正是小說家衍說高俅事的來源。3當代學者論著涉及高俅事蹟的,除了王利器教授前述一篇包括高俅在内之水滸人物考證專論外,鄧之誠 (1887—1960)教授在 1959年註《東京夢華錄》時,也引用過這則筆記,以高俅善踢毯的事來註解書中「毬杖踢弄」的一條。另翁同文 (1915一1999)教授也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據此則筆記考出高俅與徽宗、蘇軾(1036一1101)及王說(1048—1104後)的關係。翁氏一文除指出此則筆記即為《水滸傳》高俅事蹟張本外,更指出 《水滸傅》在何處改動了史實。4另外,就筆者所見,有幾位大陸研究《水滸傅》的學者,在王利器教授研究的基礎上,寫過好幾篇論高俅的文章。至於宋史學者專文考證高俅其人其事的,在九十年代初有陳紹棟教授一文。另外,1998年初李裕民教授也發表了一篇短文。5上述多位學者,除了根據上述《揮塵錄 •後錄》的記載外,6還參考了《宋史》、《宋會要輯稿》、《建炎以來樂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靖康要錄》、《玉照新志》、《夷堅志》、《兩朝綱目備要》等史籍中的零星記載,用以考辦高俅的事蹟。筆者翻閱有開史料時,發覺上述各書,尚有多則有關高俅事蹟之記載,未被採用:而宋人文集、筆記、方志、詔令中,記載高俅一家事蹟者,也有不少。筆者因此不避淺陋,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再進一步鈎尋考索高俅之事蹟,兼論高俅在宋代武將中之類型。
主要參考文獻
1、王利器:〈水滸的真人真事〉(續完),載《水滸导鳴》(宜昌:長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二輯,頁33。按該文的上半篇發表於《水滸导鳴》 (1982年),第一輯。
2、陳忧 (1613-1670後):《水游後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頁200-- 201,243 --247。
3、王利器:〈水蔚的真人真年〉(纖完),頁31:王士楨:《居易錄》,文淵圈《四康全街》本,卷七,菜5上下:阮葵生:《茶餘容話》(北京:中華替局,1959年),卷十八〈高俅〉、頁540一550:的想(撰),貞凡、顧醫、徐敏假(點校):《茶香室旅鈔•三鈔》(北京:中華香局點校本,1995年),卷三〈高俅〉,頁1040—1041。另潘永因在湾前期所绵的《末科頻鈔》也收入《挥堡錄 •发錄》這則記越,並提出此當是《水滸傅》高俅故女的來源。參見潘永因(編):<宋稗麵鈔>・文淵開く四庫金習)本,巻三,葉8下至9下。
4、孟元老(2一1147)(撰),跳之誠(注):《東京麥華錄注》(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年),巻之元 <京瓦伎藝・秘杖踢界>・買141ー142。抜:進者所引用之香港商務印楼館1961年版,揀鄂珂所編的〈外之成先生主县落作目録>職,該替最初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在1959 年出版・香港版営係城此重印。參見鄧科(編):《鄧之誠學術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456: 翁同文:<王詵生平考略>,載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1970年)・第五輯・真135ー168・
5、王利器:<水滸的真人真事> (續完)・頁31一35:歐陽健:<水滸新議>(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頁167-179: 王珏、李殿元:《水滸傳中的懸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5-106,358-360:陳紹棣:<高俅其人>,載《宋遼金史論叢》(北京:中華數據,1991年),第二輯,頁218一223:李裕民:〈歷史上的高俅及其子弟〉,《晉陽學刊》,1998年第3期,頁100-101。筆者撰寫初稿時,未引用陳、李兩教授之專論。承馬幼垣教授、曾瑞龍兄相告,僅此致謝。按陳教授一文所引史料與本文部分相同,惟觀點看法有異,請讀者加以比較。另本文不具名之評稿人指出尚在王健飛發表於1989年之<高俅生平事蹟考略——水滸人物歷史原型探源>一文,但登載之刊物不詳。後查知刊於《湖北教育學院學報》1989年2期,惟本文未見。
6、王明清這則筆記註明時胡元功所雲。胡元功是什麼人?多位學者都沒有加以考索。就筆者查檢所得,朱熹(1130-1200)的同年、後官至給事中、敷文閣學士的平江府長洲(今江蘇吳縣市)人胡元質(1127-1189)有弟名胡元功。考胡元質在紹興十八年(1148)登科,而胡元功則在龍興元年(1163)登第。胡元質登第時年二十二,胡元功概年輕十數歲,在時間上,胡氏兄弟成年時之年月距高俅之死尚不遠,大有可能從高俅之親故後人或徽、欽朝遺老處,知聞高俅之生平事蹟(按:高俅之子高堯明、姪高堯咨分別在紹興十七年(1147)及乾道三年(1167)仍活躍於宦海)。雖然我們對胡家兄弟生平所知有限,考胡元質官至給事中,生平見《吳郡志》:胡元功官至尚書,有女號惠齊居士,婿則為淳熙八年(1181)榜之狀元黃由(?-1181後):但筆者相信這個胡元功,就是告訴王明清有關高俅的事的人。考王明清這則筆記,後來又為成書於南宋中、晚期的《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所因襲,《水滸傳》中有關高俅之發跡描寫大概亦本於此。當代宋史學者撰寫高俅簡史,或旁及高俅事蹟時,也主要根據王明清的這條筆記。參見王明清:《揮塵錄·後錄》(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卷七,頁176: 章定(?-1208後):《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葉18下至19上:不著撰人:《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葉25上,113下:范成大(1126-1193)(撰)陸振嶽(校點)《吳郡志》(蘇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二十七,頁393-394:卷二十八,頁409-411:王鏊(?-1506後):《正德姑蘇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卷五十一,頁16-18:卷五十七,頁29: 鄧廣銘(1907-1998)(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高俅·俞宗憲撰>,頁406: 任崇岳:《風流天子宋徽宗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65-166:周必大(1126-1204):《文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十九<繳高堯咨轉官不當狀>,葉10下至12上。
高俅官拜太尉,晉位使相,又爵封國公。說來是官高權大,位極人臣;然而,未知何故,《東都事略》及《宋史》都不為他立傳。7而李棗 (1115--1184)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又不幸佚去了徽宗和欽宗 (1126-—-1127 年在位)兩朝,至於楊仲良(?一1184後)的《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未》,就僅保留得一條有開高俅的記載,故此高俅之事蹟,只能常羣書零星之記載逐一考辨。8
高俅的里籍,《水滸傳》倒說得不差,據《建炎以來擊年要錄》的記載,高俅確是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市)人。9至於他的家屬,《水滸傳》所說的過繼子「花花太歲」高衙內,区懂得使妖法的高唐州(按:宋代無高唐州,只有高唐縣,元初始置高唐州,今山東高唐縣東)知州高廉,自然是小說家杜撰的人物。歷史上的高俅,他的親人姓名可考的,計有他的父親高敦復(?-1123)、他兩個兄弟高伸(?—1127)和高傑(?-1127 後),他四個兒子高堯卿(?—1126)、高堯輔(?-1126後)高堯康(?—1126後) 和高堯明(?—1147後),以及高伸的兒子高堯咨(?-1167後)。
高敦復是什麼出身?《揮麈錄.後錄》並沒有提及,只說他後來建節為節度使。10《宋大詔令集》收錄有他在宣和二年(1120)五月,自崇信軍(即隨州,今湖北隨州市)承宣使建節為建武軍(即邕州,今廣西南寧市)節度使之詔令,詔中稱許他「謹畏而小心,沈毅而有勇,任職滋久,而未管有過,遇事不擇,而居惟盡忠」。11這篇官樣文章說他「有勇」,看來他是靠槍棒謀活的人;不過,他任武官在高俅發迹之前,還是在高俅顯達之後,就未可考。李若水 (1093—1127) 在高俅死後翻他的舊賬,說高俅「以市井之流,售充胥史之役,論其人則甚賤也」。12看來高敦復即使真的武官出身,也是地位低微的,是故從沒有人稱高俅為將家子。似乎高敦復出任武職,一直做到節度使,完全是父憑子貴。高敦復在宣和五年 (1123)正月病卒,徽宗賜謚「康簡」,真可說是庸人多福。13
高俅三兄弟中,誰人居長,羣書記載很不一致,高俅是老幾,學者並沒有結論。惟據徽宗在宣和七年 (1125) 十二月賜高伸的一首七律的詩題,筆者認為高伸居長,高俅行二,高傑最幼的可能性最大14。和高俅及高傑不同,高伸一直任文官。據《揮麈錄·後錄》所説,高伸「自言業進士,宣赴殿試,後登八座」。高伸是否真的進士及第?文獻無徵,筆者相信他也是靠高俅得以入仕。他不擧無衒,貪婪無比,因高俅得寵而擔 任顯官,歷任殿中監、戶部尚書、保和殿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最後充資政殿大學士。但當徽宗退位,高俅失勢後,他先被貶貴降職為延康殿學士,最後落得個抄家身敗的下場。15高傑的生平事蹟,史書所載,比高伸還少,他和父兄一樣出任武官,然他無才無德,無功無勞,倚着高俅之势,累宫至左金吾衛大將軍,他也像高伸一樣,當高俅失勢後,被貶職抄家。16
高俅四子一侄,在高俅當權得寵時,不過是一班乳臭未乾的小兒,但憑着高俅之恩蔭,卻都輕易取得百戰沙場的老將以及官海浮沉多年之土大夫所難得到的高位。計高堯卿官至岳陽軍(即岳州,今湖南岳陽市)承宜使,高堯輔做到安國軍(即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承宣使,高堯唐做到桂州(今廣西桂林市)觀察使,高堯明做到戶部員外郎,高堯咨做到直秘閣。17其荒謬之地方,誠如李若水所言:「子孫弟姪或塵政府,玷污班。兒童被朱紫,媵妾享封號:膳奴廊卒,名雜仕流。」。18當然,一榮皆榮,一枯盡枯,高俅兄弟失勢後,他們的子姪也就樹倒猢猻散,再也不復當年之富貴。19
主要參考文獻
7、王玨認為高俅敗壞軍政,是造成金人長驅之罪首,所以《宋史»不為其立傅。此說有誤,按被指為宜和六賊的蔡京、蔡攸 (1077--1126)、王黼 (1079-1126)、童貫 (1054—1126)、梁師成 (2—1126)和朱勔(1075--1126)等人,《宋史》均有立傅。高俅無傅,也許因官方記錄散佚所致。考徐夢莘(1126—1207)忘《三朝北盟會编》,訪求蒐集雨宋之际之大事史料,可謂豐富詳盡,在蔡京等人相開條目下都至少附有小傳,惟在高俅相關條目下,卻沒附有什麼碑傳記載,可見商俅之史料散佚,連徐夢莘也蒐集不到。另李裕民教授則認為商俅既無滔天大惡,亦無赫赫政績,故(宋史)不為其立傳。然筆者認為史料散佚,大概才是《宋史〉不能為高俅立傅的原因。参克王珏•举殿元:《水滸傳中的懸案》頁96,李裕民 :(歷史上的高俅及其子弟),頁101。
8、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收入趙鐵寒(1908-1976)(主編):《宋史資料萃編》(台北:文害出版社,1967年11月),第二輯,卷一百四十八,葉6上下。
9、李心傳(1166—1243)。《建炎以來联年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一,葉16上(以下簡稱《要錄》),施耐庵(?-1365後)(集撰),羅貫中 (?ー1400後)(篡修):《水滸全傳》,鄧振鐸 (1898-1958)1953 年點校本(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頁16。
10、《揮麈錄.後錄》,頁176。
11、不著撰人(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卷一百零五<高敦復建武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制>,頁391。
12、李若水:《忠愍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再論高俅劄子>,葉6下。按李若水載靖康元年(1126)五月先後兩度上奏,反對惟高俅舉哀,又請削奪高俅官爵。他這兩度劄子提供了不少有關高俅生平之史料。《宋史·李若水傳》曾節錄過這兩篇劄子的內容,王利器教授之專論曾加以引用。參見脱脫(1314-1355)(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卷四百四十六<李若水傳>,頁13160:王利器:<水壺的真人真事>(續完),頁32。
13、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本,(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職官七十七之十二、十三>(以下簡稱《會要》):《揮塵錄·後錄》,卷五,頁139。
14、《水滸傳》稱高俅為高二,然高俅三兄弟誰人居長,群書中所記就很混亂。據《揮塵錄·後錄》所載,高伸為兄,高俅為弟;但《玉照新志》及《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則以高俅為兄,高伸為弟。然《靖康要錄》又以高傑為兄,高伸為弟;而《要錄》又以高傑、高伸都是高俅之兄;然《三朝北盟會編》又以高俅、高伸為兄,高傑為弟。王珏先後引用元人王明山及明人李宗山之考辨,但仍未確定高俅排行第幾。學者們大概失看了徽宗賜高俅的一首詩。該詩載於岳珂(1182-1242後)的《寶真齊法書贊》內,詩題作「宣和己巳冬祀大禮,卿以執綏待玉輅回鑾,禮畢以詩來上,俯同元韻賜伸,乃宣至俅、傑」,據此,高氏兄弟之行第,應該如徽宗所稱,以高伸為長,而高俅、高傑為次。參見《揮塵錄·後錄》,卷七,頁176;王明清(撰),汪新森、朱菊如(校點):《玉照新志》(與《投轄錄》合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三,頁49;《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葉19下(按:此處引朱勝非(1082-1144)的說法):汪藻(1079-1154:《靖康要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一,葉1下:《要錄》,卷一葉30下至31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三十二,葉8上(以下簡稱《會編》)。王珏、李殿元:《水滸傳中的懸案》,頁102-104:岳珂:《寶真齊法書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徽宗皇帝御製冬祀詩御書>,葉6上至7下。
15、據《會要》所記,高伸在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十七日已以殿中監之銜上《六尚供举敕令》(按他的文階官,在政和三年〔1113〕二月時為朝請郎)。至政和五年 (1115)二月欽宗冊為太子時仍任殿中監(照《夷堅志》的說法,這書是他人代编的)。按劉安上(1069一1128)的《給事集》,收有高伸殿中監轉官制。考劉安上於政和元年冬召為中書舍人,執掌誥命,而高伸在政和元年十一月己任殿中監,二記正脗合 :惟不知高伸遷何官。按從殿中監陞侍郎再遷尚書,在正常情況至少要数年。考《夷擊志》一則記載,稱高伸為尚書,而事緊於在張商英(1043一1122)為相時。考張商英在大觀四年 (1110)六月拜相,政和元年八月能,然這並不是說高伸在政和元年二月至八月間已陞任尚書,只是宋人以他後來擔任最高的官位來稱呼他。他在重和元年(1118)閏九月前已任戶部尚書,在任內,他奉宰相鄭居中 (1059一1123) 之命,推行講畫經費局,徵收諸路白地錢,又增加酒價商税,以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後來受到朝臣反對,懷疑高伸乘機斂財。他在宣和四年(1122)前,授保和殿學士(按:初名宣和殿學士,政和中始置,至宣和元年 〔1119〕 二月改名保和殿)、提舉上清寶錄宮兼侍讀,在同年十二月再擢保和殿大學士,後再加资政殿大學士之職。他在銷康元年四月自資政股大學士降為延康殿學士,到了同年十二月更落職。在洪遊 (1123一1202)《夷堅志》的筆下,高伸是一不學無術之徒,連政典為何都不知。他在芽康二年(1127)正月金兵破城後被抄家,紛人搜出大量金銀,其為官贪墨可知。陳均(1174-1244):《九朝编年術要》,文淵閣 《四庫全街》本,卷二十六,葉53下:卷二十八,葉43下至 44上:《會要》,〈刑法一之二十七〉、〈袋制三之四十四〉、〈職官十九 一、十、十一〉:《端康要錄》,卷一,葉4上:港四,葉31下:卷十一,葉1下:劉安上:《給幫樂》,文淵開《四庫全書》本,卷二〈酸中監高伸股中丞王遜轉官〉,藥14上下:卷万<附錄• 劉安上行狀〉,葉15上下:徐度(?-1138俊):《卻掃編》,文淵開《四庫全替》本,卷中,葉2下至了上:《要錄》,卷一,葉30下至31上:《宋史》,卷二十〈徽宗紀二〉,頁 384—386:卷一百六十四<職官志四 •殿中省〉,頁3880—3881:洪道(提),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梦局點校本,1981年),丁志,卷三,頁557—558:23《寶真齋法書赞》,卷二 〈微宗皇帝傅旨御批〉,葉10下至11上。
16、《靖康要錄》,卷十一,葉1下至2上。高傑在靖康二年正月,亦以隱匿金銀,自左金吾街大將軍降充左街率府率。
17、《靖康要錄》,卷四,葉2上,31下:卷五,葉42下至43下:《要錄》,卷四十八,葉9上:卷九十一,葉1上:《西要》,〈職信三十六之一百二十二〉。考王珏看到了《會要》這一條記載,知道高俅有兩兒名堯康、堯輔,但錯誤理解了《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紀〉一條記載,把徽宗第三十子、封為昌國公的趙柄 (1122一1132),作為高俅的兒子「高柄」,另不知高俅尚有兩兒名堯卿、堯明。參見王珏、李殿元:《水滸傅中的懸案》,頁99一104:確庵(?一1164後)、耐庵(?一1267 俊)(編),崔文印(笺證):《靖康稗史笺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靖康稗史之三 • 開封府狀笺證》,頁95—96。
18、《忠愍集》,卷一,葉6下至7下。
19、考高堯明和商凳咨在紹興、乾道年間還擔任知縣之類的小官,參見本文第六節。
高俅的出身,《水滸傳》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寫。研究高俅事蹟的學者,都點出《水滸傳》的說法,實在本於《揮鑒錄•後錄》的記載。只是在小說裹,小蘇學士蘇轍 (1039--1112)取代了大蘇學士蘇軾,而又杜撰了臨淮(即泗州,今安徽泗縣)閒漢柳世權和開封藥舖老閟董將士二人,另又在一些次要情節加以改動而已。20不過,《揮麈錄•後錄》並没有記載高俅投靠東坡前,出身是什麼?《水滸傳》描寫高俅人蘇門前,是「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自少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毯」。又說他「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後來不合做了一個富人王氏之兒子幫閒,因教唆主子花天酒地,而給主子之父去開封府告了一狀,結果被判四十脊杖,發配臨淮三年。21有趣的是,《水滸傳》這段高俅前史,竟然有點事實根據。考上文提到的李若水,他所寫的〈再論高俅剳子〉,便揭露了高俅不光彩的出身,說高俅「以市井之流,嘗充胥史之役:論其人則甚賤也,恃愚矜暴,數被杖責,考其素則甚兇也」22。我們從李砦水的記載,可以知道高俅出身市井,家世卑微,發迹前還多次吃過苦頭,屢遭杖責。
據《揮鹽錄•後錄》的記載,高俅的發迹,始於做東坡的小史,開鍵在成為王詵的親隨。這一點卻有學者懷疑,尤其是蘇轼有否用高俅為小史的問題上。 23筆者以為王明清的記載可信,首先,在高俅是否做過胥史的問題上,李若水兩道上奏宋廷的劄子,一再稱商俅「以胥會之才,和「省充育史之役」,正是《揮毫錄•後錄》說法可信的有力旁證。24其次,當我們細心考查東坡一家與高俅關係時,會發現王明清所言非為道聽途說。
考《揮璽錄•後錄》記,高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即定州),留以子曾文崩(按:即曾布,1036--1107),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俅)極其富實,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25東坡與高俅的關係,雖然除了這條材料外,我們暫找不到其他的佐證:但是,我們卻能找到比 《揮肇錄•後錄》 更早、更一手的記載,證明王明清所說高俅不忘東坡知遇之恩,厚待其子弟之說法不假。
大陸前數年幾位研究東坡第三子蘇過 (1072—1123 ) 生平事蹟的學者,在撰寫蘇過年譜及校註他的《斜川集》時,引用了蘇過好友趟鼎臣(1068?—1124後)在政和六年 (1116)所撰一首贈蘇過的七律,這首七律的詩題作「聞蘇权禁至京,客於高殿帥之館,而未管相開,以詩戲之」。這首詩的詩題清楚不過地揭示了一個事實,蘇過與高俅交情決非泛泛;一方面蘇過入京而選擇住在名聲不好的高俅家,令趙鼎豆也笑他「朱門伹識將軍第,陋巷難逢長者車」;另一方面,高俅居然紆尊降貴,去款待當時尚未完全獲平反的元祐大豆子弟的蘇過。倘二人不是如王明清所說的有那機的淵源,實難以解釋。26
其實,倘我們仔細閱讀蘇過的《斜川集》,我們還會找到二人交往的蛛絲馬迹。按《斜川集校注》的編者舒大剛從《永樂大典》輯出一篇蘇過的佚文,題為「代人賀啟」,而舒氏在其《三蘇後代研究》之〈蘇過年譜〉卷下考定此啟是蘇過在政和二年(1112)代人賀張近 (?—1112後)帥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而作。不過,筆者以為這篇佚文其實是蘇過贺高俅陸任股前都指搬使而寫的。大概因高俅名聲不好,編次蘇過文集的人,就隱去了受賀人的身份,而且改為蘇過代人作賀啟。當然,舒大陶既不是考索高俅生平的「有心人」,又不是專業治宋代制度史的學者,故此,就看不出文中稱受賀人「進長殿酸,荐分符節」,乃是專指出任殿帥而領節度使的人。也就不會聯想到這篇賀啟的受文人,很有可能是他在〈蘇過年譜〉裹提到的高殿帥高俅。我們若細味賀啟中那些歌功頌德的話,例如稱受賀人「德並河嶽,學參天人;才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徘徊趙魏,磨畏之如敵國長城:出人巖廊,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君臣合德,始終一心。頃居宥密之司,夙見倚毗之重。方佇登庸於元老,遂懷補外之高風」,再比對 《揮蹙錄•後錄》等有關高俅事蹟之記載,我們會發現,蘇過這篇賀辭,用在高俅身上,從身份、官位以至與徽宗的開係,都是貼切不過的。另外,蘇過在這篇賀啟之末,稱「舊掃門屏,久暌星躔。豈圖樗散亡餘生,復託監書之未吏。溝中之断,雖絕意於青黄:轍下之鱗,猶有冀於升斗。丘山之惠,没齒何忘?燕雀之情,賀廈敢後」?倘受賀人碓是曾照顧過蘇氏兄弟的高俅,蘇過這番滿帶感恩的話,也是很合適的,而非泛泛之諛詞。 27附帶一談,王明清的《揮塵錄·第三錄》曾記一事,稱在宣和中,蘇過遊京師,居於景德寺。一日忽然獲徽宗宣召,命他作畫。徽宗表示知他是東坡之子,善畫窠石,故有此召。蘇過畫成,徽宗稱数之餘,腸酒厚貨遣歸。蘇過忽來此好運,就像做夢一般。28這個故事倘不假,我們會問,是誰向徽宗推薦蘇過作蜚?筆者以為最有可能的人,就是既與蘇過交好,又知他的行蹤,而又是徽宗親信的高俅。考這則故事,王明清註明是胡元功所傳述。而胡元功正是在《揮璽錄•後錄》中傳述高俅事蹟的人。我們若從這層關係去推想。則在這條筆記中,使蘇過交上好運的人,就呼之欲出了。29
雖然在東坡現存之詩文中,我們尚找不到高俅任東坡小史之記載;但高俅善待東坡子弟的事,卻文獻有徵。根據以上的考證推論,我們可以相信《揮麈錄 •後錄》之記載不假:高俅有感於東坡知遇及舉薦之德,當他發迹後,就善待東坡子弟以報故主之恩。
高俅在東坡門下當了多少年胥史?王明清沒有說。筆者相信至少有一段日子,高俅才會給人「筆札頗工」之考語而蒙東坡賞識,而絕不會像《水滸傳》所說那樣在蘇府住上幾天便走。《揮麈錄•後錄》記,高俅從東坡小史成為王詵的親隨,始於東坡出寸中山之年。考東坡在元祐八年 (1093) 九月後離京出知定州,30則高俅人王詵之門當在是年底。檬《揮麈錄•後錄》所說,高俅要到元符末(即元符三年,1100)才巧遇徽宗,並成為徽宗藩邸親隨。這樣說,高俅在王詵府中當親隨首尾共七年。可惜,目前見到之史料,除了《揮靈錄• 後錄》多外,我們尚見不到其他關於高俅與王詵往來之記載。不過,既然我們已能證明東坡父子與高俅大有淵源之專不假,而大量史料又證實高俅為徽宗藩邸舊人(譁見下文),而翁同文教授考證王詵生平之專論,又充份論證了東坡與王詵的深厚交情,以及徽宗登位前與王詵之親密交往,31則高俅因東坡之薦而成為王詵親隨之說法,筆者認為可能性甚高。
高俅第二個主人王詵,是北宋有名之大畫家。他宇晉卿,是太祖功臣王全斌(908—976)之後,仁宗 (1022—1063 在位)朝馬軍副都指揮使王凱(996-1061)之孫。他在神宗 (1068_1085 在位)即位初,以左衛將軍選尚神宗二姊蜀國長公主(1051--1080):不過,他生性風流,行為不檢,神宗因姊姊之故才一再優容他。蜀國長公主在元豐三年 (1080)病逝,神宗怒他不善待公主,將他貶黜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後徙潁州(今安徽阜陽市)。他在哲宗 (1086—1100 在位)登位後恢復駙馬都尉名位;32不過當哲京親政後,他因與舊裳之關係,並不大得意。論號份,他是哲宗和徽宗的姑叉。據《揮麈錄 •後錄》所說,封為端王的徽宗在藩邸時,因「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王詵與這個内姪投緣,自然因彼此對書畫古玩有共同的喜好所致。另外,也可能看出徽宗「貴不可言」,而加以交結。33《揮麈錄•後錄》說王詵在元符末(按:哲宗於元符二年正月崩,元符末當指元符二年底至三年初) 見任樞密都承旨,在上朝時在殿廳待班,碰見徽宗。徽宗問王詵借用篦刀理餐。王詵見徽宗喜愛此物,就在當晚派高俅送一式兩副的篦刀到端王府給徽宗,結果給高俅帶來好運。34這條記載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是王詵派高俅送禮的時間。考徽宗在紹聖三年 (1096)三月封端王,並出就傅,到元符二年 (1099)五月出居外第35,這脗合《揮麈錄•後錄》所載,王詵派高俅送禮到端王府後「踰月」,徽宗就登位的說法。不過,李若水後來說高俅「事上皇三十年」,若從靖康元年上推,到元符二年,首尾為二十八年,還差兩年才足三十之數。當然,李若水可以將二十八年籠統的稱作三十年;36不過,筆者懷疑高俅人徽宗藩邸可能略早於元符二年底,蓋依《揮塵錄 •後錄》之說,高俅入徽宗藩邸才一月,便被徽宗倚為腹心,乃是不可想像的事。第二是王詵在元符末年的職位。王明清稱王詵當時任樞密都承旨;不過,考諸羣書,未有記載王詵在哲宗朝擔任過樞密都承旨。而據 《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在元符元年 (1098)四月,當曾布對哲宗言及王詵之「薄劣」時,哲宗的反應是「亦晒之,訖不用也」。要說哲宗會用他為樞密都承旨之可能實不大。另王詵在元符二年聞九月,因被御史劾奏匿藏婦人,又教令寫文字投雇,及虛作逃亡之事,而被哲宗罰銅三十斤;然《資治通鑑長編》在此條下只稱他為駙馬都尉,而沒有提及他當時職位是樞密都承旨;此外,邵伯溫 (1056—1134)的《邵氏聞見錄》及《宋史》均載他在建中靖國元年 (1101),因做不成樞密都承旨而遷怒尚書右丞范純禮 (1031—1106),可見他在哲宗晚年任樞密都承旨之可能性不高。反而,人稱「大王都尉,的王師約(1044—1102)卻在元符三年初,徽宗即位後曾任福密都承旨。筆者懷疑是胡元功或王明清錯把「大王都尉,的宫位誤作「小王都尉」的。37
主要參考文獻
20、對於《水滸傳》將高俅原本投靠蘇軾,改寫為投靠蘇辙的事,王玨曾提出一些解釋,他認為《水滸傳》作者不想將他醜化的高俅,與大文豪蘇軾扯上關係,故此將這筆賬算在「比較風流倜儻」而又與王詵關係好的小蘇學士蘇轍頭上。不過,小説作者大概不想羅織蘇辙太甚,故不明說是蘇辙,而只說是「小蘇學士」。另外,王玨又點出《水滸傳》在哪些次要情節作出改動,例如王詵叫高俅送徽宗的禮物,從原來的篦刀改為玉龍筆架與鎮紙玉獅子。最後王玨提出不相信高俅真的當過東坡的小史,以為《揮壁錄·後錄》是野史不足信。《水滸傳》作者為何有此改動,很難知真實理由:不過,王玨卻不知東坡要比乃弟與王詵關係更深,情誼更厚,另外,說蘇轍比較風流,也不知何所依據。關於高俅與東坡之淵源,下文將會詳述。《揮壁錄·後錄》雖屬私家記述之「野史」但可信程度之高,非王玨能所料。參見《水滸全傳》,第二回,16—18:王玨、李殿元:《水滸傳中的懸案》,頁95—105,頁97—98。
21、《水滸全傳》,頁16。又據香港《水滸傳》學者馬幼垣教授的研究,現藏於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和藏於日本日光輪王寺的《京本增補校正全像水滸志傳評林》均載高俅落難在靈州靈璧縣,而不是臨淮:另照顧他的是軍吏柳世雄,而不是柳世權。當然,靈州(今寧夏靈武市西南,一説在寧夏吳忠市南金積鄉附近)既不屬宋所有,而靈璧縣(今安徽靈璧縣)也不在西北之靈州,而在臨淮(泗州)附近的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小説家之言自然不辨地理,不計歷史。又考《隴右金石錄》,在政和元年六月,擔任會州(今甘肅靖遠縣)懷戎堡巡檢的人亦名柳世雄。不知事屬巧合,還是《水滸傳》作者確有所本。是條資料,承同門好友曾瑞龍兄賜告,僅此致謝。參見馬幼垣:く牛津大學所藏明代簡本水滸殘葉書後》,載馬幼垣:《水滸論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頁8:張維(?—1941 後)(編):《隴右金石錄》,民國三十年(1941)甘肅省文獻徵集委員會校印本,收入《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七輯,<宋上>,頁508—510。
22、《忠愍集》,卷一,葉6下。
23、參見註釋20。
24、《忠愍集》,卷一く駮不當為高俅舉掛箚子》、<再論高俅箚子>,葉5上下,6上下。
25、《揮壁錄·後錄》,卷七,頁176。
26、舒大剛:《三蘇後代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蘇過年譜》,下,頁250;亦見曾棗莊、舒大剛:く蘇過年譜>蘇過(撰),舒大剛(等點校):斜川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收入,頁778。趙氏這首詩,可參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葉3上。
27、考張近字幾仲,開封人,《宋史》有傳。他進士出身,官至顯謨閣直學士。他與東坡父子均有交,但他從未當過「殿巖」之殿帥,也未建節。他當非該賀啟之受文人。參見《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張近傳>,頁11145—11146:《斜川集校注》,卷十,頁719—720:舒大剛:《三蘇後代研究》,《蘇過年譜》,下,頁234;《文忠集》,卷四十八《跋東坡與張近帖》,葉19上下。
28、《揮麈錄·第三錄》,卷二,頁240。
29、關於胡元功的事蹟,參看註釋6。
30、按李燾以東坡初除定州,在元祐八年六月,後不行,而再除定州在九月。畢沅(1730—1797)考定東坡離京赴定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孔凡禮則仍以東坡出知定州在九月二十六日之後。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1995年),卷四百八十四,頁11515(以下簡稱《長編》):畢沅:《續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57年),卷八十三,頁2109;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三十二,頁1102-1104。
31、參見註釋4。
32、王詵早在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因牽連在東坡烏台詩案中,被追兩官勒停。元豐三年公主病重,神宗為安慰公主,就恢復王詵原官。公主病卒不久,神宗查出王詵對不起公主之事,便將他貶謫。到哲宗即位,在元祐元年(1086)九月才復駙馬都尉、登州(今山東蓬萊市)刺史。參見《會要》,く職官六十六之十》:《長編》,卷三百零一,頁7333:卷三百八十七,頁9428;《宋史》,卷二百四十八く魏國大長公主傳>,頁8779—8780;卷二百五十五<王凱傳附王詵傳>,頁8926。
33、關於徽宗與王詵之交往,除見於《揮壁錄·後錄》卷七之記載外,亦見載於《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這條記載引述蔡京子蔡條(?—1126後)之説,稱徽宗在「潛邸時獨喜讀書學畫,工筆札,所好者古器山石,異於諸王。又與駙馬都尉王詵、宗室令穰遊。二人者,有時名,繇是上望譽聞于中外」。另外蔡條在其《鐵圍山叢談》裏也記徽宗為端王時與王詵互贈名畫之事。參見《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く花石網>,葉16上下;蔡絛(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園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年),卷四,頁78。
34、據莊綽(?—1150後)所記,「河間府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為靶,鈒鏤如絲髮」。大概王詵送給徽宗就是此物。參見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年),卷上,頁33;《揮盛錄·後錄》,卷七,頁176。
35、《宋史》,卷十八く哲宗紀二》,頁344:卷十九<徽宗紀一>,頁357:《長編》,卷五百十,頁12146。
36、《忠愍集》,卷一,葉6下。
37、據邵伯溫所記,王詵在徽宗繼位後,曾上简子向徽宗求為樞密都承旨。徽宗自然答允,但仍垂簾聽政的向太后(1046—1101)反對,說王詵浮薄,若任之為都承旨,就會壞了樞密院之事。向太后以另一駙馬王師約在哲宗朝為此官稱職,主張改由王師約出任。徽宗只好照辦。邵伯溫又說,曾布早就想排擠范純禮,於是對王詵訛稱他做不成都承旨,是因范純禮的反對。王詵信了曾布的話,深恨范純禮,後來他因館伴遼使,而乘機誣告范純禮在押宴時,席間語犯徽宗之名。結果范被罷右丞之職。《宋史·范純禮傳》所記相同。這裏附帶一談王詵與曾布的關係。有人或許認為曾布既然在哲宗前說王詵的壞話,徽宗及王詵後來就不可能派高俅去聯絡他,爭取他的支持。筆者以為持這種看法的人,倘有注意曾布後來能向王詵中傷范純禮的事實,就知二人的關係並不是外人所看那麽簡單。以曾布投機的性格,為迎合哲宗而罵一下王詵,但暗地裏和他眉來眼去,暗通消息,又有什麽稀奇?筆者以為要判斷二人是友抑敵,不能只看曾布一次罵王詵的事,而要全面查察二人以前及以後的動作。王師約是太祖功臣王審琦(925—974)玄孫,治平三平(1066)尚英宗長女徐國公主(?—1085),據《宋史》本傳所載,他在徽宗即位初,的確曾任樞密都承旨。邵伯溫所記不誤。至於他在哲宗朝曾否任都承旨,則暫無其他佐證。據《宋史·職官志》所載,似乎王師約在哲宗朝並未在樞府供職。又據近人梁天錫之宋樞密院制度專著的樞密都承旨表,王師約和王詵在哲宗朝均榜上無名。綜合羣書所載,王詵在元符末年擔任樞密都承旨的說法,當是誤傳。參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年),卷五,頁43—44;《宋史》,卷一百六十二く職官二》,頁3801;卷二百四十八<楚國大長公主傳>,頁8779:卷二百五十く王師約傳>,頁8820:卷三百十四く范純禮傳》,頁10279;《長編》,卷四百九十七,頁11834:卷五百十六,頁12270;梁天錫:《宋樞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上冊,頁111。
高俅深得徽宗寵信的緣故,《揮塵錄•後錄》說得非常戲劇化,稱高俅奉王詵命送禮至端王府,遇上徽宗在園中蹴毯,高俅時來運到,偏巧他精於此道,而得以在徽宗前露了一腳好功夫。徽宗大喜之餘,馬上把高俅留下作親隨,而王詵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欣然同意高俅過府。高俅此後日見親信,後來徽宗登位,他作為從龍之臣,就得以飛黄騰達。徽宗後來對其他藩邸舊僚言及高俅得到重用的原因,也半真半假地說因高俅踢得一腳好毬所致。這也就是《水滸傳》說高俅原來叫高毬的故事張本。38《揮麈錄.後錄》條記載的真實性有多少,實在教人懷疑。無疑,徽宗喜愛踢毬,而高俅出身市井,會此道也不出奇,但若說高俅因踢毬而獲徽宗寵信,就似乎有渲染誇張的成份。高俅是徽宗的從龍之臣,宋人官私方面都有充份可信的記載。徽宗御筆稱高俅「係随龍」,又賜書閣名日「風雲慶會」;而在拜他為股前都指揮使的制誥中說他「嘗事潛藩,永肩誠節」:在拜其父為節度使之制誥中,又稱許他「事予潛满,赤心左右,一節初終,如宋昌以謀議而戴孝文,如王常以親信而從光武」;另在拜他為使相之制誥中又說「爱念勳勞之舊,孰可與:載惟攀附之良,見存無幾」:而李若水則說他「事上皇於潛邸,夤緣遭遇,超躐顯位」,「事上皇三十年,朝夕左右,略無裨益」。39以上種種,都可以見到徽宗與他不比尋常的君臣開係。筆者以為高俅受到徽宗無比的寵信,並不因他工於筆札,或是會踢幾腳好毬所致。筆者懷疑徽宗對他信任不替,除了他對主子忠心耿耿,以及知情識趣外,最重要的是他在徽宗從藩王人繼大統之事立下大功,才會得到徽宗無比的信任。
上文所引、徽宗在宣和二年五月拜高俅父為節度使的制誥,將高俅比作輔助西漢文帝(前180—前157在位)、東漢光武帝(25—57 在位)得成帝業之從龍功臣宋昌(?一前176)和王常 (?—36),40正好透露了高俅當年的從龍之功,並非跟在主子後面坐享富貴那麼簡單,他實在出過大力,才膺日後之厚賞。考徽宗繼位,並非一帆風順,宰相章惇 (1035—1105) 就極力反對:只因向太后堅持,而知福密院事曾布帶頭附和太后之議,才使徽宗登上寶座。41筆者以為徽宗也像其他兄弟一樣,眼見哲宗多病而無子,早就暗中營謀帝位。42他交結駙馬王詵和宗室趙令穰 (?—1144),博取好學儒雅之名。43但筆者以為徽宗能得到向太后的歡心,大有可能是受到王詵等所造之與論影響。而徽宗得立的開鍵人物曾布,所以肯全力支特徽宗,除了想取章惇之相位自為外,筆者懷疑徽宗曾暗中做了收買工夫,而高俅正做了居中聯絡的人。據《揮壅錄 •後錄》所載,當年東坡出守定州,本來想把高俅交託給曾布的;只是曾布以府中胥史已多,才沒有接受。曾布雖然没有做高俅的主人,准二人按理不會不相識。紹聖以後一直在京的曾布,相信與高俅仍有過從。微宗要找人聯絡曾布,高俅自然是最理想的人選。後人都以為徽宗荒唐糊塗,然觀乎徽宗在登位前之從容不逼姿態,以及他在位時的用人手段,他也有其精明的一面。寓居澳洲的道教史權威柳存仁教授,二十多年前早從徽宗註《道德經》之精審,洞察出徽宗其實「深思睿然,精通南面術。」44《揮壘錄•後錄》 說徽宗在元符末年一次朝堂相遇中向王詵借篦刀,而王詵選擇晚上派高依送禮。我們有誰知道王詵送上的,是否真的只是一對雖然名貴,但價值終有限之篦子刀那麽簡單?筆者懷疑曾被神宗斥貴「泄漏禁中語」的小王都尉,45這次其實送上極其重要的情報。而信差高俅就是王詵極為信任,不會洩漏秘密的人。大概高俅的縝密與幹練為徽宗所識,故此就耍求留用高俅。至於踢毬之事,筆者以為是徽宗故意說出去以掩人耳目。
概而言之,筆者相信高俅所以後來得到徽宗無比的寵信,絕不會是只因曉得踢幾腳毬那麼兒戲,而是由於他居中聯絡(甚至有份說服)以曾布為首的大臣,支持徽宗繼統有大功所致。他在徽宗幕邸的地位,由於史料缺乏,暫難確定他是否徽宗的謀主。不過他對徽宗忠心不貳,兼出謀獻策,奔走聯絡,是可以肯定的。後來徽宗將他比作漢文之宋昌、光武之王常,大概他當年是加此評定高休之功勞的。
主要參考文獻
38、《揮壁錄·後錄》,卷七,頁176:《水滸全傳》,頁17—19。又據江少虞(?—1145後)所記,不獨徽宗好此道,連他的兒子高宗(1127—1162在位)亦精敏於蹴鞠之藝,並置供御打毬供奉之官。參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五十二,<蹴鞠>,頁684。
39、《會要》,く職官七十七之十二、十三》;《揮麈錄·後錄》,卷七,頁164;《宋大詔令集》,卷一百零二く高俅拜太尉制>,頁377;く高俅除使相制》,頁379:卷一百零五く高敦復建武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制>,頁391;《忠愍集》,卷一,葉5下至6下。
40、考宋昌是漢文帝為代王時代國之中尉,當京中大臣平定諸呂,使人迎立文帝時,他力排眾議,主張文帝接受。文帝入京,他隨駕保護,又先入京打探情況,確知並無危險,就還報文帝。文帝抵渭橋(即中渭橋,約在今陕西咸陽市東北二十里),他又使京中大臣向文帝恭行臣禮。文帝即位,任他為衛將軍,統率南北軍,並以掖贊之功,封壯武侯。他是文帝得以自外藩入繼帝位的最大功臣。至於王常是光武帝守昆陽(今河南葉縣)時之部下,劉玄(23—24在位)稱帝時任為廷尉,行南陽(今河南南陽市)太守事,封鄧王。但他一直忠於光武兄弟,光武稱帝翌年四月,即率眾來降,光武歡喜地説:「吾見王廷尉,不憂南方矣。」並即拜他為左曹,封山桑侯。是年十一月,光武拜他為漢忠將軍,副岑彭(?—35)南征,光武當眾稱許王常,説他「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參見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卷十三,頁435—443;卷三十九,頁1240—1243,1256—1257:卷四十,頁1302,1305—1306。
41、據《九朝編年備要》所記,入內內侍省都知梁從政(?—1101後)初給事哲宗生母欽成皇后(1052—1101),後受欽成之命,交結章惇,使章惇支持哲宗同母弟簡王似(?—1106)繼位。章惇後來果然抬出以長當立申王佖(?一1106),以禮當立簡王來反對微宗繼統。從這裏可以側面見到哲宗晚年,諸王已為繼位問題而暗中交結大臣。又據《會要》所記,當向太后召見梁從政,詢及定策之事,他即附和章惇。到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當徽宗親政後,即算舊賬,由宰相韓忠彥(1038—1109)出面,將梁從政參劾貶逐。參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五,葉23下至24下:《長編》,卷五百二十,頁12356—12367;《宋史》,卷二百四十三く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傳>、く欽成朱皇后傳》,頁8630—8631:卷二百四十六<吳榮穆王佖傳>、《楚榮憲王似傳>,頁8722—8724:卷四百七十一<章惇傳>,頁13713;<曾布傳>,頁13716:《會要》,《職官六十七之三十三>。
42、蔡絛的《鐵圍山叢談》揭露了徽宗在登位前許多營謀帝位的舉動,絕非意外地被人捧上帝位。又《九朝編年備要》載有一個隸太史局的人郭天信(?—1109後)在元符末年得以常出入禁中。徽宗每退朝,他就遮道多次向徽宗說他當得大位。後來徽宗登位,對他信任有嘉,給他恩澤如從龍之人,後來連蔡京也在他攻劾下罷相。這個人顯然是徽宗佈在內廷的線眼,為徽宗刺探情報,才得到徽宗的寵信。此外,周輝(1124—1195後)的《清波雜志》也記載徽宗在登位前一再暗使人持其生辰八字,到相國寺找一個會術數的人陳彥測論。徽宗登位後,即厚寵此人,授以高官。關於徽宗營謀帝位的問題,有人認為徽宗當時年僅十八,一直長於深宮,出居外第才數月,不該有這種智謀與城府。筆者認為若僅以年齡作為判斷一個人智計的唯一標準,那是昧於常識的淺見。歷代皇帝比徽宗即位時更年輕而更有智計謀略的,大不乏人,我們隨便的即可以舉出明世宗(1522—1566在位)、清聖祖(1662—1722在位)等好幾個。即在北宋,仁宗、神宗即位時亦不過十多歲,不比微宗繼位時年長;但他們心智卻早已成熟。另一方面,筆者認為長於深宮的人,不但不會缺乏歷練,反而在險惡的環境中生活,更會比常人在政治上早熟。有人認為徽宗就算要聯絡曾布,也不會派出投他不久而身份屬家僕的高俅。筆者以為,徽宗不派隨他日久的心腹,而改派新參且毫不起眼的家僕高俅聯絡曾布,正是他厲害之處,正是他教其競爭對手疏於防範之手段。徽宗成功的地方,就是不讓普通人看出他暗中營謀帝位。他不會像欽成后一樣,竟派內侍中地位甚高的梁從政去聯絡章惇,而招人話柄。參見《鐵圍山叢談》,卷一,頁1,5—6:卷三,頁41—42;《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七,葉43上:周煇(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六,頁241—242。另外研究宋徽宗的任崇岳教授,指出徽宗既非紈姱子弟,也不是昏庸之輩,他在哲宗諸弟中,是營謀帝位最積極的一個,既將自己扮成好學儒雅的人,又交結有時譽的大臣,製造興論;另外暗中占卜休咎,覬覦大位。又懂得收買宫內宫外的人,刻意討好向太后。參見任崇岳:《風流天子宋徽宗傳》,頁1—4。考徽宗如何博得向太后歡心,任氏也沒有列出史料證明。筆者以為能出入宫禁的王詵和趙令穰等人,是最有可能為微宗在宫中營造美名的人。
43、趙令穰是太祖的五世孫,字大年。他是北宋末書畫名家,尤工草書,生平喜歡收藏晉、宋以來的法書名畫,他自年青時已有好讀書及能文之美名,在哲宗時因端午進畫扇而受到哲宗賞識。大概因他能出入宮廷,而又是徽宗的同道,故徽宗刻意的交結。他官至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到高宗朝仍健在,曾與蘇轍之孫蘇籀(1091—1164後)有交。參見不著撰人:《宣和畫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く墨竹挺節凌霜圖一>,葉4下至5上:鄧椿(?—1167後):《書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く侯王貴戚>,葉2上下;舒大剛:《三蘇後代研究》,<蘇籀年譜》,卷下,頁331。有人認為王詵名聲不佳,一直不為哲宗甚至向太后所喜,徽宗如何會藉他博取時譽?筆者以為王詵不為哲宗等所喜容是事實;但他是飲譽士林藝壇的大名士,是蘇軾及其門下一大批士大夫始終引為知己的人,徽宗藉王詵爭取蘇軾一班元祐舊臣的支持,是很化算事,也實在情理之中。
44、參見柳存仁:《道藏本三聖注道德經之得失》,載柳存仁:《和風堂讀書記》(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上冊,頁25,27,31—33。是條資料蒙何漢威學長提示。
45、《會要》,《職官六十六之十》。
徽宗對助他登位之人,均予以酬庸,曾布得償所願,取代章惇為相,王詵也擢至節度觀察留後,46而高俅也獲徽宗提拔,步步攀陞。《揮麈錄•後錄》說高俅在徽宗登位後,「眷渥甚厚,不次遷拜。…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47大致得其實。考高俅在徽宗朝任官的最早記載,是哲宗、徽宗朝直臣鄒浩 (1060一1111)的文集《道鄉集》所保存的一道〈高俅轉官制〉。考鄒浩在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前除中書舍人,大概在是年十—月前遷吏部侍郎,則他撰這道制誥當在是年八月至十一月間。48這道制誥沒說高俅轉什麼官,制文只說「亟遷秩序,密奉軒墀,朝廷盛選也,朕不虛授。惟爾試藝應格,逢時致身,故以是命焉」。我們從其辭句推敲,高俅是經過試藝(按指武藝)的手續,而獲遷在宫禁隨侍徽宗的優差。至於職位,相信是供奉官閤門祗候一類的武臣近職。高俅本來頗通文墨,不過,由於出身不好,兼没有科第之資歷,就不像其见高伸走文官的路子,而改從武官之途仕進。49
《水滸傳》說徽宗「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抬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50考《水滸傳》這段描述,除了最後說高俅只用半年便當上殿帥這一點不確外,其餘都大致不差。正如上文所述,徽宗的確先讓高俅經試藝後,做他駕前的小使豆。然俊又找機會給高俅立邊功,以便擢陞他。章穎(1140-1217)的《宋南渡十將傅》即記:「先是,高俅誉為端王邸官露,上(徽宗) 即位,欲顯擢之。舊法,非有瀀功不得為三衙。時(劉)仲武為邊帥,上以俅屬之 ,俅竟以邊功至殿帥。」51因史料散佚,及宋人可能有意刪落高俅事蹟的記載,除了《宋南渡十將傳》這條記載外,晢時沒能找到有關高俅因立邊功而得到擢陞的具體記載。當然,籠統的說高俅立有邊功的記載,在《宋大詔令集》所收有關高俅的三篇制誥都有提及。按政和七年 (1117)正月,高俅拜大尉的制文即說他「暊臨邊寄,國奏戰多」:而宣和二年五月其父高敦復建節的制文更說他出使敵國有大功,說他「虧者杖使節以載驅,街王命而抗論:凜凜而義形於色,諤諤而言皆匪躬。相如入秦,爛然完壁之蹟;蘇武守節,壯哉引佩之辭」。另宣和四年五月他拜使相之制文,也說他「將幣婆庭,耀使華於漠北:收疆戎塞,聳戰氣於山西」。52
高俅在何年隨劉仲武 (1048—1120)立邊功?考徽宗在崇寧二年(1103)開始向西疆用兵,同年六月收復湟州(今青海樂都縣)。這次軍事行動,劉仲武以蘭州(今甘肅蘭州市)第九將的身份從征有功。九月,以劉仲武權領湟州事。是年十二月,劉仲武又以洮西安撫之身份率兵解循化城(即一公城,今甘肅夏河縣北)之圍,以功改知河州(今甘肅臨夏市),進東上閣門使。崇寧四年 (1105) 四月,劉仲武再破夏兵於清平寨 (即溪蘭宗堡);不久再破吐蕃,復西寧州(今青海西寧市),進客省使、榮州(今四川自貢市)防樂使。53考高俅在崇寧四年五月以容省使副龍圖閣直學士林塘 (?—1110後)出使遼國,54他隨劉仲武出征,似當在崇寧二、三年 (1104)間,當劉出任湟州、河州守豆時。高俅立了什麼戰功?居然可以在短短四、五年間越過諸司使臣一級而陞任橫班使豆次高職位的客省使?筆者以為高俅的戰功都是因人成事居多,劉仲武顯然揣摩到徽宗的心意,有戰功都給高俄一份。高俅有了 「邊功」,微宗也就名正言顺的不次提陞他。
高俅從横班使臣擢陞為「禮繼二府」的三衙管軍,相信是賞他崇寧四年五月出使遼國之功。據睪書所載,高俅這次出使,過程充满火藥味。考遼國於是年四月因西夏之求援,遺使質問宋廷,為何攻西夏而取其地。五月宋廷即派林塘使遼,並以高俅為副。林是宰相蔡京的死煎,他出使前,蔡暗中授意林攄,要他故意激怒遼廷而啟靈。林撼抵遼後,果然採高姿態,既盛氣凌人,又處處與遼人抗爭。他見到遼主,又力數西夏的不是,並抗言遼國不能約制貴備西夏,現在憑什麼責怪宋廷,還要為西夏講話?林撼一番辭鋒凌厲而出其不意的話,弄得遼廷君臣不知所答。到他辭行準備返宋時,遼廷要他向宋廷代遞遼方的國書,仍要求宋歸還在夏境所建之城寨。但林撼的回答很強硬,不肯應承遼的要求。遼人大怒,不顧外交禮儀,將林撼、高俅等住的驛館的所有供應停止,斷他們食水糧食三天,又羈留他們多月,才讓他們返宋。林撼這次與遼人針鋒相對,絕不妥協,反對他的人說他是「怒鄰生事」,但在徽宗看來,他實在為宋廷爭了很大的面子,替宋廷出了口惡氣。結果林摭陞任禮部尚醬,以賞出使之功。55上文引述的制文,吹噓高俅前都指揮使職事,以使相之身統領禁軍。徽宗在制文褒對高俅溢美不止,說他「智敏而行完,才宏而量博:弧矢之威天下,妙臻百中之能,詩禮之帥中軍,雅著異聞之善,:又說他「峻更三帥之雄,嗣董周廳之次;侍殿陛者幾二十載,護貔旅者踰百萬夫。號令嚴明,肅和門而無犯,軒墀邃密,拱宸扆以攸寧」。在這些善於舞文弄墨的翰林學士筆下,出身市井而實在見不到有什麼將略的高大尉,居然成為文武全才的儒將。這裏我們把這些宫樣文章抄下,為的是立此存照,讓我們在下一節裹,比較一下高俅在失勢後宋廷對他的評價。
高俅並無大勳大功,二十年間而能位極人臣,做到「出將人相」,只為徽宗對他的信任,要他統領禁旅,把關看家。宣和五年正月,高俅之父病死,本來要丁憂守制;但徽宗御筆下旨,實行「奪情」,要他繼續統率禁軍,隨身護駕。至於他能否打仗殺敵,整肅軍伍,就不在徽宗考慮之內。他由始至終,都不過是徽宗的家臣家將,他的武將生涯因徽宗登位而始,亦因徽宗之退位而終。
主要參考文獻
46、《宋史》,卷十九く徽宗紀一》,頁359—360:卷二百五十五く王詵傳>,頁8926。考蘇軾亦於元符三年四月獲赦返內地居住,不知道是否王詵、曾布等為他説情所致。
47、考《長編》載徽宗登位後,優遷他的「隨龍人」多人官職,相信高俅也在其中,只是他當時地位尚低,故史籍不載其名。參見《長編》,卷五百二十,頁12381—12382:《揮麈錄·後錄》,卷七,頁176。
48、四庫館臣認為這道制話不被删落,而能保存下來,是因為鄒浩之子「編類之時,蒐采未備,去取亦未盡當」。又鄒浩在建中靖國元年何月出任中書舍人不詳,據其文集三處自述以及李幼武(?—1163後)所記,他在建中靖國元年任舍人,至是年郊祀時已遷吏部侍郎。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載鄒浩在是年八月已為中書舍人,而考《宋史·徽宗紀》,是年郊祀在十一月。以此推論,鄒浩任中書舍人,不晚於是年八月,而在十一月前。參見鄒浩:《道鄉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提要》;卷十一<追感董敦逸夢授侍郎>,葉2上:卷十六く高俅轉官制》,葉6下:卷三十六く至明弟墓誌銘>,葉12下至13上:卷三十八く黃陵廟祝文二首》,葉1上下:《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葉5下:《宋史》,卷十九<徽宗紀一》,頁362—363;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三く鄒浩吏部侍郎>,葉12上下。
49、考《長編》載,在元符二年七月己未,「軍頭司引見殿前、馬軍司揀試到散祗候等殿待長行八十人試藝」,其中箭法突出的兩人換左班殿直,並減三年磨勘。相信高俅應的試藝,和上述的類似。以高俅從無階無品的王府小吏入仕,這次轉官,應該還是在三班使臣之內,而加閤門祗候之近職,就可稱得上「密奉軒墀」,而高俅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能得到這職位,已算是超授了。參見《長編》,卷五百十三,頁12200;《道鄉集》,卷十六く高俅轉官制>,葉6下。
50、《水滸全傳》,頁19。
51、章穎:《宋南渡十將傳》,《芋園叢書》本,卷一<劉錡>,葉1上下。
52、《宋大詔令集》,卷一百零二(高俅拜太尉制>,頁377—379:卷一百零五<高敦復建武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制>,頁391—392。
53、《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九,葉5上,19上至20下:卷一百四十,葉1下,13上至15上:《宋史》,卷三百五十<劉仲武傳》,頁11081—11082:李事(1161—1238):《皇宋十朝網要》,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月),第一輯,卷十六,葉8上,12上至13下。
54、《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六,葉13上。
55、《宋史》,卷二十《徽宗紀二〉,頁374 :卷三百五十一く林據傳〉,頁11101112:《皇宋十朝網要》,卷十六,葉13上至14上。據《皇宋十朝網要》載到崇寧四年八月戊子,宋廷再派禮部侍郎劉正夫(1062—1117)充北朝國信使,「以林越街命未還」。可見林、高二人被遊方國留至少三月多。考蔡京之子蔡條對林據這次出使,有甚為沒染之記裁。替中稱林據抵遊後堅持不行遼人之禮儀。又說林據在遼人亮出兵刃,逼他看虎國時,常從人皆泣,他卻一點也不怕,還不管遼人之忌譯,稱國中老虎為南朝之狗。最後林摅不屈而還。總之,在蔡條之筆下,林據似要比簡相如更剛猛英雄。至於高依的表現如何,是同樣不屈?還是在「從者泣」之內,察條就沒有提及。參見《鐵園山叢談》卷三,頁54。
高俅及其家人得以高信厚祿,權勢薰天,並非有何本事,只是憑徽宗的恩寵。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人以宋敗盟,分兵兩路南侵。徽宗見金兵來勢沟沟,自問無法應付危局,而朝臣又請求讓太子監國時,在是月二十四日,他就乾脆把這個包袱丢給他那個少不更事的兒子欽宗,實行内禪,自已退居太上皇。在靖康元年正月初二,當金兵尚未兵臨城下前,大概在童貫等慫恿下,徽宗帶同心腹近臣,包括蔡仫、高伸等離開京師,向南方逃跑。手握兵權的童貫與高俅率勝捷軍及禁軍扈從。56一朝天子一朝臣,徽宗才退位。宋廷朝臣便馬上奏劾以蔡京為首的徽宗佞臣。太常少卿李網 (1083--1140) 便率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書,痛劾童賞、王黼、蔡收、朱動、李彥及高俅誤國,請將他們貶黜。其中高俅被指「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白衛,失禁旅之心」。而太宰白時中 (?-1127)也轉風駛舵,在靖康元年正月,將京中禁旅不堪作戰之責任,歸答於「外則童貫失陷,内則高俅不招刺,軍政不修」。57考在徽宗在位時,人們縱使不満,地不敢對炙手可熱的高殿帥有何公開的批評。最多以童謠的方式,間接表達他們對高俅一家弄權專横的不滿。58為討好主子,宋廷那些負貴寫制誥的文臣,只會搜索枯腸,引經據典,拼命對高俅歌功頌德,寫下一篇又一篇上一節所引、肉麻不堪的制文。當高俅兄弟隨徽宗南逃後,在靖康元年正月十二日,宋廷就開始對徽宗之佞臣包括高俅兄弟開刀,差官往他們家,査抄他們之金銀家當,要他們送納國庫,並且明令「若有徇情隱庇或轉為藏隱,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行軍法」。59
當高俅在京之府第被抄查時,他們父子兄弟在泗州亦成為喪家之犬。大概高俅與童貫等在是否繼續往南逃往鎮江府(今江蘇鎮江市)之事上惷見不合,童貫就假傳徵宗之命,令高俅留在泗州守樂,不得南行。據高俅奇給留在京師之親弟高傑書信所言,童貫不許他們護駕,甚至不讓他們見到徽宗。有術士要跟隨,就給童貫之親兵勝捷軍射倒。60童買逭番舉動,倒讓高俅可以和他劃清界限。當宋廷朝臣對童貫等猛加奏劾,指他們欲挾持徽宗以謀叛時,髙俅就僥倖脱身,不受牽連。他很快便以疾請解軍職,返回京師。61早在正月六日,欽宗便已委任他的母舅、比高俅更壞大事,更教人寒心的王宗港(?一1131後),以殿前都虞候權管幹股前司公事,收回高俅執掌十多年的兵權。62高俅肯乖乖的交出兵權,欽宗倒不像對付童貫般對付他。到是年三月,當宋廷己將蔡京、王黼、童貫、染師成等人或誅或貶時,欽宗居然還以他扈送徽宗有勞,進封簡國公。63是年四月三日,徽宗從鎮江返京,高俅選因此得以加官檢校太保。但是月底,朝臣卻不放過高俅一家,御史台追究當日高伸、高堯明跟隨高俅南逃,而擅離職守之罪。欽宗已算寬大,只將高伸自資政殿大學士降為延康殿學士宫祠,將高堯明追五官勒停。這時,高俅己是自身難保,能有這樣的結果,己算欽宗手下留情。64
高俅在是年五月十四日病卒,得年多少不詳。因他死時還帶着開府儀同三司的頭街,依照儀制,使相薨,朝廷要掛服舉哀。大常博士李若水本管此事,即連上兩道劄子,反對欽宗為他掛服,並列舉高俅生前過惡罪狀,認為高俅得全要領而死,實在便宜了他,認為他實在死有餘辜。在李若水等眼中,高俅最大之罪過,是他敗壞軍政,遵致金人南侵時,宋軍無力抵禦。至於高家為宫貪墨聚飲,還在其次。李若水痛言金人能長聒京師郊甸,「正坐軍政刓激,士不賈勇」,而宋軍弄到如此不堪作戰,正因高俅「撫恤無恩,訓練無法,,卻叉「占役上軍,修築第宅,或借權費以縮私歡,,他說弄到喪師辱國之田地,「雖三尺之童皆知童貫、高依粟坡軍政之故」。而高俅「久握兵柄,衡與童貫分內外之寄,厥罪惟均」,既然童貫受到遠察之貴,天下稱快,而高俅未就典刑便死了,實在不公亚。他指出高俅之死,「中外交賀」:借要為高俅舉哀行褸,實在沒有道理,應該追奪他的官爵,以為奸諛之戒オ是。65
欽宗大概想給徽宗留一點顏面,不想馬上清算乃父最寵信之近臣,對於李若水的箚子的回應,是先在是月十六日,下旨暨不為高俅翠哀,並正式宣佈高俅之罪過,稱他「率領筆兵,敗壞紀律,果有言章」,給他的處分是追降其官職,而其子孫有倖冒的,亦與降等授官 。兩天後擦吏部之報告,再下旨正式追奪高俅檢校大保和開府儀同三司的加官,而高俅三個兒子堯卿、堯輔、堯唐則自承宣使和觀察使降授右武大夫及武功大夫,仍領遙都刺史,餘宫並奪,至於高俅諸孫就免追究。對於欽宗如此寬大處理高俅一家,以李若水為首的朝臣,自然不肯罷休。聖旨一出,即有朝臣(疑叉是李若水)再嚴効高俅,這道奏章比李若水前兩道節子,更具體指出高俅敗壞軍政的過悪,現錄如下:
謹按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夤緣辛會,致位使相、檢校三公。不思竭力圖報,乃敢自恃昵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凡所招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權倖。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教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士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歛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管他業,雖禁車亦皆僦力取直,以為衣食。全廢教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会免教;無錢者又营生廢教。所以前日綴急之際,又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己求和,實俅恃寵營私所致。贪財誤國之奸,不減蔡收,偶有司失刑,遂免遠竄,得終牖下。令來止追前官,不惟不足以厭公論,亦無以誡後來。66
在朝臣之壓力下,欽宗最後在五月二十一日再下詔,追奪高俅奉國軍節度使和簡國公的職街,至此,高俅所有官爵都被削奪。不過,朝臣仍未罷休,繼續有人指責高俅誤國,好像王褻(?一1131 後)在是年六月底上奏時,便指禁衞精兵,「高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閒,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間池台矣;京城廢管之地,今為苑票甲第矣。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人,以待暴容」,最後弄到「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67
高家作惡多端,天道不爽,他們的報應發生在是年聞十一月底金兵攻陷汴京後。在玉石俱焚之情況下,己失然的高家子弟,自然是眾矢之的。首先在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開寶寺大火,宋廷下令將鄰近的高俅賜第拆掉,將木材賣給百姓。68到了靖康二年正月二日,高伸、高傑兄弟被女侍檢舉私藏金銀不肯繳納,二人立被降職,而他們一家子食墨所得的家財,就盡數被充公,轉奉金人。69
高氏一門的家財被充公了,更大的報應是高伸兄弟最後連命也保不住。在靖康二年二月,金人押送北末宗室大臣家屬往北方,高俅一家當年威風一時,現時也就逃不過玉石俱焚之劫,他們一家在被收押之列。高伸在是年五月前身死,而高傑與及高俅幾個兒子大概都慘死異域。僥倖逃出虎口,似乎只有高堯明和高堯咨。70
對於高俅敗壞軍政,間接導致汴京失守的事實,繼統的高宗是清楚不過的,71宋廷的文豆,也就沒有放過己成落水狗的高俅,繼續對他口誅筆伐。除了李綗繼續痛罵高俅外,曾在螬康年間掌權的吳敏 (?---1133),便對高宗說:「自蔡京、王黼壞文,高俅、童質壞武,網紀大亂」,72把靖康之難的責任都推在蔡京、高俅等宣和佞豆上,那就可卸去他們自己的貨任。
不過,高宗對高俅並沒有太大的個人惡感,且高俅兄弟已死,對高家就不再追究。為表示寬大,高宗還在紹興元年十月,在朝臣的反對下,仍給起復的高堯明,授宣教郎並知建康府溧水縣(今江蘇溧水縣)的小官。考高堯明知溧水縣,一直做到紹興四年(1134)二月才離任。73此後,高堯明還當過溫州永嘉(今浙江永嘉縣)知縣,到紹興十四年 (1144)五月,又以右朝散大夫出知明州之鄞縣(今浙江鄞縣),直至十七年 (1147)七月離任。明州軍號為奉國軍,曾是高俅所領之節度州,高堯明出任乃父生前所領節鎮屬縣縣令,也算是巧合。高堯明以後之事蹟不詳。74除高堯明外,高宗也在紹興五年 (1135)七月,授子高堯咨右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一職,雖然不算皇恩浩蕩,但在高家破敗之餘,也算是特恩。高堯咨浮沉官海多年,在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按:孝宗〔1163—-1189 在位〕己纖位),做到無為軍巢縣(今安徽巢湖市)知縣,本來他以措置召募萬餐營卒一百零三人有功,獲轉一官:但權給事中周必大以高堯咨並無功勞,封還誥命,反對給他遷官,周之意見後得到宋廷的接納。高堯咨在乾道元年 (1165)至三年 (1167) 曾知池州東流縣(今安徽東至縣)。他後來官運如何,就史所不載。75
高家第三代的情況,根據岳飛 (1103—1142)孫子岳珂所記,到了寧宗 (1191一1224 在位)之世,已到了坎坷貧困的境地。奇籍南方的高伸的子孫,以及流落在開封的一支高氏後人,分別在嘉定十二年 (1219)及十六年 (1223),將徽宗賜給祖宗之書帖,輾轉寶給岳珂,賴以活命。76在筆者目前可見之史料,高俅之後代事蹟可考的,僅此而己。大概高俅的後代沒有什麼長進,可補祖宗過失的人物,故此,自南宋以降,除了王明清替高俅留下一條筆記式的小傳外,似乎沒有人為高俅寫過一篇像梯的墓誌銘或行狀。明朝人記在蘇州曾找到他的堉並蓦碣,然卻是真假難辨。77世事難言,高俅事蹪湮没無聞百載後,想不到他的名宇,卻憑小說家生花妙筆,再得以在人間傅開。對高俅不幸的是,在小說家渲染下,他從此成為家傳戶䁱的大奸臣、大惡棍。
主要參考文獻
56、考童貫與高俅護駕之兵,《靖康要錄》的作者與周必大均稱童貫帶勝捷軍三千·高俅帶禁軍三千:陳東(986—1127)則稱童贯帶兵二萬:惟《要錄》則記二人率軍三萬五千。按宜和末年,宋軍自黄河兵敗後,京中禁旅人數大減·連勝捷軍在内·童貫、高俅應不可能帶走幾萬軍隊,疑《要錄》誤。又徽宗對高伸一直总能有嘉·據岳珂所記·徽宗在高伸每年生日時,特許他前二日受賜·另給他許多額外恩數·故徽宗出走,也命高伸隨從。參見《靖康要錄》·卷三·葉23上:《文忠集》·卷三十·<徽猷閣待制宋公暎墓誌銘》·葉7上:《要錄》卷一·葉16上:《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紀四》,頁417:陳東:《少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登聞檢院再上欽宗皇帝書》·葉10上:《寶真齋法書贊》·卷二·葉10下至11下。
57、李網:《梁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二く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葉1上至3上:《會编》,卷二十七,葉14上。
58、在南宋初年,大臣張網(1083—1166)上奏時,提到在微宗時,正言陳伯强因指資高俅「妄造聖語」,便馬上得罪被貶。可見高俅的權勢。又據南宋人之筆記所載,當徽宗龍臣何執中(1044—1117)居相位時(按:何於大觀三年(1109)拜相),京師有童謠說:「殺了穜窩割了菜,喫了羔羊兒荷葉在。」時人以指童貫、高俅、蔡京和何執中。參見張綱:《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七く駁陳伯張恩澤指揮》,葉2上下:曾敏行(1118—1175)(撰),朱杰人(點校):《獨醒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九,頁86。
59、《靖康要錄》·卷一·葉24上下。
60、《少陽集》,卷一《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葉12上下。據南宋人之筆記所載,徽宗等抵泗州,童黄坐在帳中,而令高俅(原文寫高球,當為筆誤)於南山把隘。後徽宗在十多日後始抵浙中。見趙彥衛(1140—1205後)(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6年),卷七,頁122。
61、高俅什麼時候稱病自泗州返京不詳,考陳東在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上書,提到從高傑家書,知道高俅被童贷勒令留在泗州之事,則高俅返京,最快當在是年二月。見《會編》,卷三十二,葉7上至8下:《揮壁錄·後錄》,卷七,頁176。
62、考欽宗即位時,他便向徽宗提出罷免曾與他爭奪儲位的鄲王楷(?—1127後)之皇城司職位,另外又提出以他的母舅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接掌高俅殿前司的兵權。對欽宗的要求,微宗均同意。按王宗濋是欽宗生母顯恭王皇后(1084—1108)的兄弟,其父是德州刺史王藻。排輩份,王宗濋是太祖開國功臣王審琦的六世孫。當高俅交出殿前司兵權時,因殿前副都指揮使姚古(?一1127後)統兵在外,故王宗濋以殿前都虞候權領殿前司。到六月姚古援太原失利革職,王便陞任殿前副都指揮使,真除殿帥。史稱王宗濋「素驕貴,不能任事,自高俅領殿前,紀律馳廢,既敵國入受,遽命宗濋,識者為之寒心」。高宗在紹興元年(1131)三月談到王宗濋時,也指出「宗濋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考張邦煒教授在其論微宗、欽宗父子在靖康年間之反目一文中,曾論及欽宗以王宗濋取代高俅,以取回京師兵權,另張氏也認為高俅隨徽宗南逃,未必報知欽宗,另也論及高俅在泗州與童貨反目後,先期回朝後,為欽宗封為簡國公之理由。參見《资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欽宗內禪》,葉9下:《皇宋十朝網要》,卷十九,葉6下至8上:《宋史》,卷二十三く欽宗紀》,頁425,433:卷二百四十五く后妃傳下·微宗顯恭王皇后傳》,頁8638;《會編》,卷二十八,葉4下至5上:翟汝文(1076—1141):《忠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く賜權管幹殿前司公事王宗濋辭免殿前都處候恩命不允韶》,葉6下至7上:《要錄》,卷四十三·葉4上:胡寅(1098—1156)(撰),容肇祖(1897—1994)(點校):《斐然集》(與《崇正辨》合本)(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3年),卷二十六く吳國太夫人王氏墓誌銘>,頁578—579:張邦煒:《靖康內訌解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頁74—78。
63、《少陽集》,卷一《登聞檢院再上欽宗皇帝書》、く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葉10下至19上:《靖康要錄》,卷三,葉9下:《會編》,卷三十一,葉2下至3下:卷三十二,葉14上至15上:卷四十五,葉1至2下。考張邦煒教授認為欽宗竞將「分明有罪」的高俅加官晉爵,是策略的運用,志在分化微宗親信。見張邦煒:《靖康內訌解析》,頁78。
64、考《靖康要錄》所記,高俅再在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加檢校太保。考同書卷三已記高俅在是年三月四日,自檢校少傅加檢校太保:而今又加檢校太保,似不當,疑三月四日加檢校少師,四月十六日始加檢校太保。見《靖康要錄》,卷四,葉20下,31下。
65、 《忠愍集》,卷一《駁不當為高俅舉掛箚子》、《再論高俅箚子》,葉5上至8上。
66、《靖康要錄》這裏只說臣僚上言,沒明載是何人上奏,比較此奏的措辭用語,與李若水前引兩道箚子相近,疑是李若水所撰,只是《忠愍集》漏收此奏。參見《靖康要錄》,卷五,葉42下至43下。
67、王襄此奏題為「上欽宗論彗星」,考靖康元年六月壬戌(二十七),「彗出紫微垣」。王襄此奏大概上於六月底。考王襄責備高俅之餘,他自己後來敗軍失律,被資為寧遠軍(即容州,今廣西容縣)節度副使,到紹興元年三月始以赦敍復為正義大夫。參《宋史》,卷二十三く欽宗紀》·頁429:趙汝愚(1140—1196)(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四十五く上欽宗論彗星·王襄撰》,頁480:《要錄》,卷四十三,葉12上。
68、這所賜第是徽宗在宣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賜給高俅的,才不過五年多,便化為鳥有。又高俅第被拆毁以資作柴薪事,《會編》繫於靖康二年二月一日。參見《會要》,く方域四之二十三》:《靖康要錄》,卷十,葉50下:《會編》,卷七十八,葉4上下。
69、《靖康要錄》,卷十一,葉1下至2上:《會编》,卷七十四,葉2上下。77 據《會編》所載,高伸在靖康二年五月十八日前已身死。他是怎樣死的?史所不載,看來多半死於金人之手。參見《靖康要錄》,卷十一,葉48下:《會編》,卷一百十二,葉6上下。
70、據《會編》所載,高伸在靖康二年五月十八日前已身死。他是怎樣死的?史所不載,看來多半死於金人之手。參見《靖康要錄》,卷十一,葉48下:《會編》,卷一百十二,葉6上下。
71、高宗對於徽、欽末年京師禁軍不堪作戰的情況,十分清楚。他在紹興元年正月便對臣下言及他在靖康年間,曾對欽宗痛陳「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即渋」。參見《要錄》,卷四十一,葉10下至11上。
72、李綱撰寫《靖康傳信錄》,為自己辯護的同時,又竄改了陳東的宣和六賊説法,將高俅的名字加入,而去掉本來的王黼。《宋史·李網傳》的作者照抄《靖康傳信錄》,於是教人誤以為高俅名列宣和六賊之中。參見《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二《靖康傳信錄》,中,葉9上下:《宋史》,卷三百五十八く李網傳》,頁11245:《少陽集》,卷一《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葉12上下:《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二《吳敏》,葉2下。
73、當時朝臣程俱(1078—1144)反對給高堯明授官,但高宗仍依例授官,並給他敍官為宣教郎,沒有歧視他。參見程俱:《北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十九<繳江東大使司辟持服人狀》,葉11下至12下:《要錄》,卷四十八,葉9上:《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溧水縣廳壁記》,葉22上。
74、高堯明何時知永嘉縣不詳,相信在出知鄞縣前。參見張津(?—1169後)(修):《乾道四明鬪經》,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五冊,卷二く鄞縣縣宰題名>,葉27上:胡矩(?—1227後)(修):《寶慶四明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五冊,卷十二《鄞縣縣令》,葉4下:王環(?—1448後)(編集):《弘治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卷八,頁23。
75、《要錄》,卷九十一,葉17上:《文忠集》,卷九十九く繳高堯咨轉官不當狀》,葉10下至12上:何紹基(1799—1873):《重修安徽通志》,清光緒三年(1877)重修本,(台北:華文書局,1967年),卷一百十五く職官表志》,葉26下。
76、據岳珂所記,在嘉定十二年,有賣書帖人持着徽宗御批高伸受賜貼,在郎舍向他求售。賣帖人稱高氏孫尚居於京師(按:指臨安,即杭州)之外,「家甚窶、待此以晨炊」。結果岳珂以萬錢貿了徽宗這幅真蹟(按:據王瑞來所考,岳珂在嘉定十二年八月,以承議郎權發造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在建康(即今南京市)任官,直至十四年八月除軍器監淮東總領,徙往京口[即鎮江)。他當是在建康買到這帖子的)。到嘉定十六年十月,岳珂在揚州(今江蘇揚州市),遣間諜至河南。課者舍於一開封民家,該民家自言是高氏子孫。諜者從該民手中購得微宗賜高伸的御製冬祀詩真蹟,並帶回給岳珂。參見《寶真齋法書贊》,卷二,葉7下,10下至11上:王瑞來:<岳珂生平事跡考述》,《文史》第二十三輯(1984年11月),頁119。
77、據明人徐鳴時(?—1629後)所記,在萬暦年間,蘇州横塘鎮人趙應奎葬父黄山北麓,掘地得石碣,上書「宋高俅墓」,而碣下即其塚,據説趙應奎仍將高墓封蓋。至於碣上有否墓誌銘,徐書就沒有提及。徐氏又稱蘇州志載郡城西北隅有高師巷(疑為高「帥」巷之訛),相傅是高俅所居處。考高俅死於開封,他的墓若說在蘇州,本來難令人致信,而高俅也未曾在蘇州住過,所謂高師巷,只怕也是以訛傳訛。不過,我們不能完全否定高堯明及高堯咨等高家後人,後來有否移居或任職蘇州,並將高俅骸骨遷葬於此。另外一條不宜忽略的線索,是《揮璺錄·後錄》的高俅事蹟傳述人胡元功,正巧是蘇州人。胡元功為何能知道高俅秘史?筆者以為他多半得自高家後人。倘若我們將兩件事合在一起去推想,事實可能是這樣:高家後人將高俅遷葬蘇州,並定居於人們所稱的高師(或高帥)巷。而本籍蘇州的胡元功因為結識了高家後人,故此能夠知曉高俅的事蹟。參見註釋6,並見徐鳴時:《橫溪錄》,明抄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二,頁277-278。
高俅敗壞軍政,令宋京師禁軍在金人圍城時不堪一戰,他自是難辭其咎。南宋初年的名臣如張守 (?—1145)、胡安國1074—1138)等均痛斥高俅敗壤軍政。直至南宋中藥,理學名臣真德秀 (1178一-1235) 及魏了翁 (1178—-1237) 仍繼續指責高俅敗壞軍政之過惡,真德秀說:「自童買、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魏了翁更說:「高俅以恩被遇,則紀律盡費,僅存三萬人。靖康之禍,京師削弱,外寇憑陵,蓋基於此。78白靖康之難作,宋人就普遍將國土淪亡的責任歸罪於以蔡京為首的政、宣奸臣和佞臣:其次再咎責靖康當國諸臣。79宋人當然不敢公開批評徽宗、欽宗,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靖康之難,最要貨責的是徽、欽二帝。高俅不過是徽宗一員家豆家將,最壞不過是一隻依附人君的城狐社鼠。他作的惡、弄的權,都是徽宗所許所授。高俅本是東坡門下一個胥史,會一點拳棒,本來沒有半點領兵管軍的本事,那是他的主子最清楚不過的:偏偏徽宗要抬舉他,要他出任執掌京師禁旅的殿帥。他能不失職,就是奇蹟。事赏上,從北宋中葉開始,宋軍能夠作戰的都是在西北邊塞的西兵,而不是在京師享福的東兵。而宋室君臣對京師禁軍的要求,不是他們的戰鬥力是否強横,而是他們的紹對忠誠。殿帥的選拔,全視乎他們的可靠程度,至於他們馭軍練兵的才能,就並不重要。像高俅這種庸將,而受委擔任三衙管軍的,在整個北未實在不少見。好像繼高俅出任殿帥的王宗濋,驕慢無識,就比高俅更懷事。他後來居然信什麼六甲神兵,以致汴京失守,城破後又率眾逃遁,他誤國的貴任,只有比高俅更大。80是故,我們要罵高俅誤國,就更應罵把他放在要位的徽宗。光罵奴才,而不罵用奴才的庸主,那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高俅在徽宗諸佞臣中,己算安份,他既未似蔡京般公然坑陷正人,也沒有像王補、童貫的貪功,弄出聯金滅遼的禍根,引火自焚:也沒有像朱劻、李彥等攪到民變四起。據《三朝北盟會編》所載,當徽宗取燕雲 「成功」後,居然以為宋廷武功蓋世,竟想向西夏進攻,收復领州(今寧夏矮武市西南,一說在寧夏吳忠市南金積鄉附近),而命曾在西夏立有邊功的高俅統籌伐夏的事。徽宗御筆條蜚攻取之計,令高俅遵行。據說高俅有自知三明。不敢依旨行事,才没有挑起另一火頭。81是故,雖然宋人一直罵他是罪無可恕的佞臣,但他的過惡,在宋人心中,和「宣和六賊」相比,還是有區別的。
我們若細心去考察,高俅當權時,他聰明地採低姿態,盡量不招人忌;有時,他還在徽宗前作態表示謙退,不肯接受徽宗給他的賞賜。82他雖教文兒子弟满門貴顯,但他並不明目張膽地招權納賄,也沒有去樹巢拉幫。没有證據顯示他和蔡京或童賀一夥走在一起,狼狽為奸。當童貫護送徽宗至鎮江時,高俅便聰明的和童賈劃清界限,結果也就救了他自己一命。83高俅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他與徽宗既有特殊的淵源,他就沒必要再投靠依附誰。他只要好好侍候徽宗,得到主子的信任,就可確保富貴。而徽宗所要的,是他絕對的忠心和可靠,而不容許他結黨:要他控制着亰師的武裝力量,以釐平所有存在或潛在對帝位的威脅:而不在乎他能否把京師禁軍練成勁旅。在這方面來說,高俅己達到徽宗的要求 。他既沒有挾軍亂政,也沒有縱軍害民,他的過惡,相對其他人來說,實在末到萬惡不赦的地歩。
高俅有否嫉賢忌能,像小說裹那樣逼害武功高強的將校王進和林沖?因文獻無徽,我們不宜一口咬定有或沒有。不過,從可見的史料所載,他倒推薦過賢才。他第一個推薦的賢才,是南宋抗金名將劉錡(1098-1162)。宣和二年,微宗忽然想起已逝的劉仲武,就詢問高俅關於劉仲武兒子的情況,高俅即舉薦劉錡,結果劉錡得到徽宗召見,並得到擢用。84高俅推薦劉錡,當然有報恩的成份:不過,他有眼光這一點,也不能抹煞。高俅第二個推薦的賢才,是有儒將之稱的張撝(?-1128)。高俅在大觀二年十二月舉薦當時為通直郎的張撝,稱譽他「潛心武略,久習兵書」。並說他「曩在有司已嘗試藝,昨緣其父恩例奏名文資,比又獲賊,蒙恩改官」。又稱「其才力於武尤長,伏望特依王厚例,換一武職,付以邊任,。徽宗結果接受高俅的推薦,特授張撝禮賓副使,令樞密院給予差遭。85後來張搭無負高俅的推薦,歷任要職:他在宜和六年正月以武略大夫使金,在靖康年間,既在金兵圍城時,在京領守軍奮勇殺敵,又曾出任接伴使,刺探敵情。高宗即位後,他隨宗澤(1060一1128)在汴京一帶抗金。建炎二年(1128)二月,金兵再犯滑州(今河南滑縣),張拼當時官知滑州、果州(今四川南充市)防禦使,於是自願率兵五千往援。張在途中遇敵,雖然敵人眾多:但他死戰不退,結果陣亡殉國。86張撝雖然軍事才能遠不及劉錡,但捨生取義之節烈,堪稱賢士,高俅抱没有看錯人。高俅第三個推薦的賢才,是仁宗駙馬都尉錢鱟臻 (?-1126後)之姪錢懌( ?--1122後)。高俅於政和三年,推薦當畤官朝散郎的錢懌,由文宫轉為武職。高俅以錢懌「才カ勁強,知識明敏,留心武略,深曉兵機」,而他又「凡歷數任,壓獲強盜」。高俅即認為錢懌的才能在武備,將他轉為武官,更能發揮他的才能。徽宗准奏,錢懌於是換職為武義大夫。錢懌雖然沒有劉錡的將咯、張撝的節義,但他不失為一捕盗的能臣,他在宣和三年便以大名府路廉訪使省的身份捕除河北羣盜有功。87
毫無疑問,高俅一家都貪財好貨,都利用手上的職權,剋扣軍費,括削民脂,以飽私殘。他們後來給人搜出偌大的家財,就是明證。然而,徽、欽二朝的當政大臣,能清廉自愛的實在為數不多,若獨責高俅,也有點不公。有徽宗這樣不理人民死活,而只知享樂的皇帝,就自然有蔡京、高俅一班逢君之惡的佞臣。比起蔡京等宣和六賊,高俅所作的惡事,程度上已算較輕,而高俅明目張膽的惡事也不大多。這個出身東坡門下,而又對故主子孫能報恩的徽宗佞豆,從其所作所為,可以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主要參考文獻
78、張守痛言:「本朝之兵,自童貫、高俅等壞之,而勤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溃,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掠婴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考張守此奏日期不詳,從文中所云「伏靓建炎元年十一月詔」,疑此奏上於建炎元年十二月張守擢為監察御史時。胡安國在紹興二年八月上言,亦稱:「本朝鑑觀前代,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按真德秀之奏,上於寧宗嘉定九年 (1216)十二月,而魏了翁之奏,則上於理宗(1224—1264在位)端平元年 (1234)正月。參《要錄》,卷十一,葉23下:卷五十七,葉8下至9上:張 守:《毘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く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箚 子》,葉16下至17下:真德秀:《西山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五<江東泰論邊事狀》,葉19下至20下:佚名(編),汝企和(點校): 《續編兩朝網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5年),卷十五,頁278— 279:魏了翁:《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八《應詔封事》, 葉24下至25上。
79、好像李綱便將靖康之難的發生,理解為「靖康之初,所以致寇者,其病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其病源於春初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另外汪應辰(1119—1176)也指欽宗當國之臣「罕可稱述」,而「皆未有能稱其任」,認為沒有人值得配饗欽宗廟。參見《梁谿集》,卷一百十一<別幅》,葉10下至11上:汪應辰:《文定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く論欽宗配饗功臣疏》,葉8下至10上。
80、考王宗濋以率眾遁走之罪,責授定國軍(即同州,今陕西大荔縣)節度副使,直至紹興元年二月,高宗才以他為欽宗外家,以赦敍復他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團練使。參《會編》,卷六十五·葉1下至2下:卷六十九,葉1下至9上:《梁谿集》,卷三十四く戒饗武臣詔》,葉3上下:《要錄》,卷四十三,葉4上。
81、徽宗命高俅伐西夏,《會編》未載是哪一年。據胡寅所載,微宗在宣和七年命童貫率五路兵攻西夏,打算取天德州(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北五加河東岸)、雲內州(今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東南),但金人南侵,才收回成命。以此推之,徽宗命高俅伐西夏,當在宣和四年到六年(1124)間。參見《會編》,卷二百十五,葉7下:《斐然集》,卷十二《左朝請大夫王公墓誌銘》,頁595-596。
82、好像在政和七年七月,他便向微宗婉謝賜給他的額外從人。見《會要》,く職官三十二之八>。
83、參見註釋68。考宋人多將童貫與高俅相提並論,好像呂中(?—1247後)便批評徽宗將「高俅、童貫之徒妄加節鉞」。其實高俅一直與童貫保持距離。參呂中:《宋大事記講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治體論》,葉6上。
84、《宋南渡十將傳》,卷一,葉1上下。關於高俅薦劉錡的年月,徐規教授考為宣和二年冬或稍後,參見徐規、王雲裳:く劉錡事蹟編年》,載岳飛研究會(編):《岳飛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三輯,頁195。
85、《會要》,《職官六十一之十七》。
86、《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四,葉6上:《梁谿集》,卷五十く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箚子》、く奏知酸棗門守票捍退賊馬箚子》、《奏知再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简子》、く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援張摘勾引召募人馬箚子》,葉2下至5上:卷八十二《辨余堵事箚子》,葉11下:宗澤:《宗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七く遺事》,頁105:《會要》,《儀制十一之二十九》。關於張搗戰死滑州之事,研究宗澤的學者也有論及,只是張為與高俅的淵源,就沒有提到。參見許序雅(等):《宗澤評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34—135。
87、《會要》,く職官六十一之十七、十八》、《兵十二之二十六、二十七》。
高俅是北宋什麼頻型的武官?他在當權時,那些奉命撰寫制誥的翰林學士,幾乎要將頗通筆札,會點拳棒的高俅說成文武全材的儒將。實際上高俅的所謂邊功戰功,都是因人成事。他能夠成為徽宗朝軍職最高的武將(不算童質幾個內臣),只為他是徽宗的從龍功臣,而得到徽宗的信任所致。從太宗(976-997在位) 開始,帝皇潔邸醬臣中的武臣,以家臣家將的身份,雖無纇赫戰功,或統率三軍之オ能,卻常常渡委為樞府執政或三衙省軍,執掌軍權。88北宋統治者這種任人惟親的做法,幾乎無代無之,好像真宗(997ー1022 在位)之龍信王繼思(?一1023後)、張者(? 一1048)、崇動 (976-1045)、夏守恩(?一1037)等;89仁宗之擢用安俊(?—1044 後),莫不如此。90高俅因緣際會,成為徽宗之家臣家將,而得以統率禁旅,位列將相。在大平時期,像高俅這等庸才,佔一席高位,吃一口閒飯,還不會對國家構成太大的傷害:但一旦邊廷告急,這批在帝皇身邊而無真本事的奴才,卻常會胡作安為,或嫉賢忌能,大大破壞軍心士氣,而或帶來嚴重的後果。高俅若早死幾年,也許他的惡行會被一掩而過:偏偏金兵圈城,國將不保的時候才身死,雖然逃得過刑責,卻逃不過清議。
歷史上的高俅,自從給《水汁傳》的作者醜化為書中最大的反派後,他和他的「衙內,兒子就成為民間流傳的武將歹角典型。91説來地有點冤枉,高俅在史籍保留下來的事蹟,其實很有限:但在有限的記載下,卻仍給小説家添油添醬,成為大惡棍、大妊人,那是高氏後人(假若在元代還有)哭笑不得的事!説來有趣,在く水滸傳>襄和高俅形象相反、被尊稱為「老种」、「老种經路相公」的北末未名將种師道(1051-1126),事蹪歷歷見於史籍,但小說作者卻着盤不多,甚至没有真正出過場!种師道和高俅同卒於靖康元年金兵圝城後而汴京尚未失陷前,在宋人眼中,前者忠勇為國,後者貪庸誤國;前者文武全才,後者濫竽充数;92然前者後人所知不多,後者則幾乎無人不曉。歴史舞台與小説世界的實與虛、真與假,乃教人玩味不已的。
主要參考文獻
88、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太宗對其晉邸舊人的任用,參見蔣復璁(1898—1990):《宋太宗晉邸幕府考》,載蔣復璁:《珍帚齋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三《宋史新探》,頁60—81:至於晉邸佞臣對宋初軍事之負面影響,可參閱本書的另一篇文章く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頁87-135。
89、《宋史》,卷二百七十九<王繼忠傳>,頁9471—9472:卷二百九十く張耆傳》,頁9709—9711:く楊崇動傳》頁9713—9714:《夏守恩傳》,頁9714—9715。按《宋史·王繼忠傳》後附載真宗即位後,除上述數人外,真宗其他藩邸武臣受到擢用之名單。
90、《宋史》,卷三百二十三<安俊傳》,頁10467—10468
91、歐陽健曾從文學創造的角度,以及市民階級的立場,解釋為何高俅被《水滸傳》作者寫成大反派。參見歐陽健:《水滸新議》,頁167-177
92、關於种師道的事蹟,特別是從微宗未年到靖康之難一段,可參閱本書的另一篇文章<論靖康之難中的种師道(1051—1126)與种師中(1059—1126)>,頁551-584。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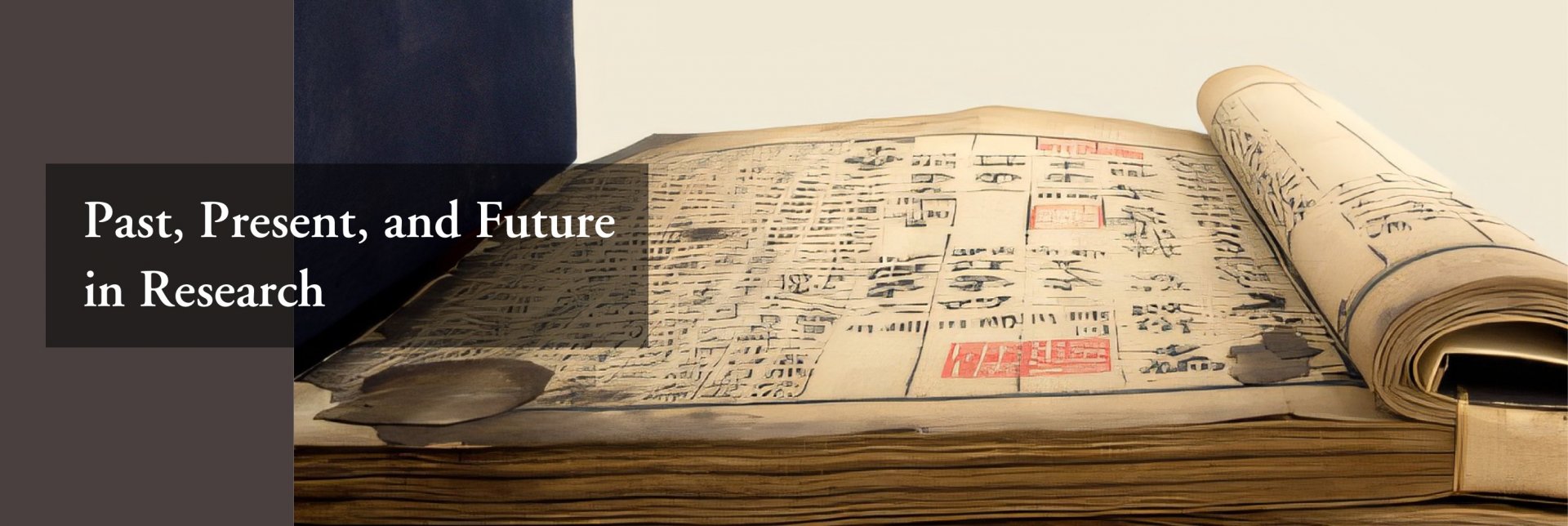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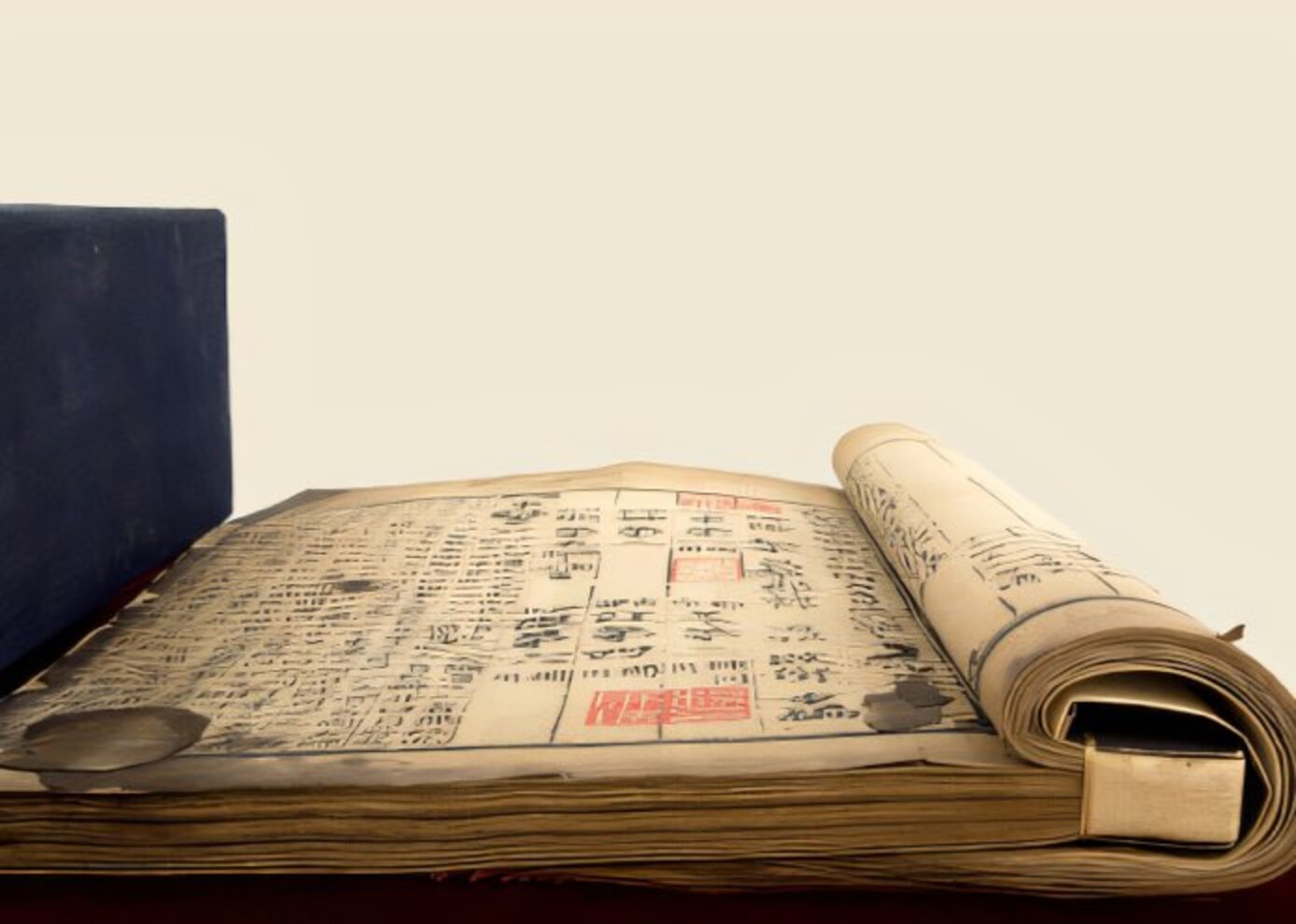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